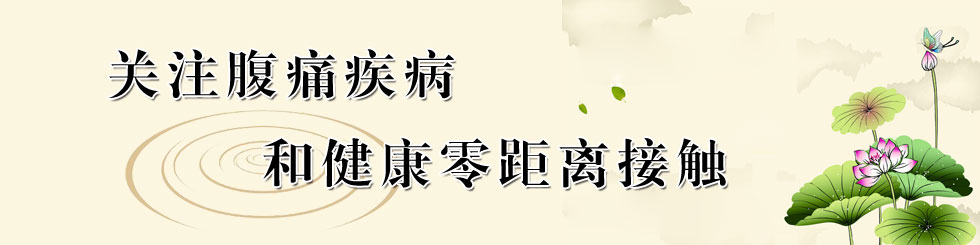|
第一卷外科狗的日常 一 春天的北平总是一天黄一天蓝的,仿佛只要霾挡住了日,人的心里往往都会生出一种日了狗了的感觉,满满的负能量让人什么都提不起劲。这种日子如果发生在周五,每个人心里仿佛都连着一根皮筋,老板一松手这货就能弹飞回他的狗窝去。 赵步理这种外科单身狗自然也想早点回去,周末的试验也不想做,他就想吃个胡同口晋阿姨的麻辣烫,然后在宿舍宅着,趁舍友不在看个小片儿爽上一发,然后上网打游戏杀杀时间。可他****的基友李有才下午骑摩托车飞出去了,锁骨刚好断了,手术于是就找他顶包了。想想以后可能这货废了一只手,以后看片儿x的时候就不能快进了也真是暗爽。 走在手术室的通道里,赵步理有时总会生出一阵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通道,这边是生,那边是死,两边的屋子是人类与人类在以一种奇妙的形式与万能的神对抗,以及妥协。有些人从这些屋子里新生出来,有些人活着进去,更好地活着出来,而又有一些人,会从另外一侧离开。 病人仰面朝天地被推着,心里咚咚地跳着,感觉周围的人长得都像救命稻草,恨不得伸手牢牢抓住。但下一秒都可能掏出个针扎你一下。只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医院的手术天花板上有一些帷幔,印着“乐观、信念、治愈、坚强、希望”,随着手术车推动的过程逐渐依次映入患者眼帘。中国人的信仰是空缺的,病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最能平静下来,安心接受着这几个词汇的灌输,内心仿佛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被放弃。 但赵步理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些的,因为他就是想回去,而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算一算再快也得12点回宿舍,虽然没有人等他,但是他也仍然不那么乐意。不光是他,路上碎碎念的人也是不少。麻醉师胡清泉,岁数不大三十过半,因脸上总是此起彼伏的痘子人称胡二麻子,这时候也一脸黑线的做着术前的准备,把该连接的管道连好,嘴上骂骂咧咧地,很难听懂他到底想干什么或者想怎么样,大意就是今天孩子妈让他陪着孩子过生日,这已经是第多少次了,他也不想故意逃避责任,干这么晚也没给个钱云云。而手术室的巡回护士杜姐和刷手护士小云俩人就像说相声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吐槽某某主任做的太慢太细,谁谁做的又快又好,今天命真是不好,今天国安的球都看不上了。 赵步理坐在手术室里,默默地发呆,像平时一样不给人一点存在感,争取也不碍事。他习惯性地核对了一下病人的姓名。 “您好,您叫什么名字?” “易米”。 台上的女人发出略带颤抖和抑郁的声音,这时候赵步理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病例上写着只有32岁,单位写着某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职位虽然不清楚,但是凭借赵步理对于女人的粗浅了解,他感觉这个眉毛细长,嘴唇微翘的有些美丽的女人散发着职场精英女性的气质,但是此刻还是像一只猫狗市场等待出售的小猫一样,一边发抖一边让人更加地怜爱。 于是赵步理大胆地说出了一句话,“您别着急,我们会轻一点下手的。” 下手,下,手…… 向日葵每天都会随着太阳从东边慢慢看到西边,然后大约在清晨的某一个时刻猛地甩过头去。所有在场的几个人都一下子停下来手中的工作,把头甩向他,甚至还咣当掉了一把钳子,然后还能听到小云咽了下口水的声音。 赵步理心里也是一万匹草泥马,想自己一百年也不和人主动搭讪,一辈子头一回想好好和人说句话,没想到是这样的效果。她面前的女人也是闭上了眼。 “谢谢医生” 他仿佛看到女人好像笑了一下,但是还是很和善、有风度地化解了这一场尴尬。杜姐立马发挥了巡回护士的能力,嚷嚷了一句“姑娘你别怕,有我们在呢他们手底下都利索着呢,就是嘴不利索,大夫您赶紧给把被子给弄弄”。 赵步理一听到有人帮他立马就平复了,赶紧做点什么赶紧做点什么,哦对,弄弄被子,下面要画切口消毒了。 然后他一步上前把没有完全盖住上身的被子往下拽到了肚脐。 “你!——” 女人什么也没说,只是闭上了眼睛,任凭****全露也不敢乱动。杜姐急得火冒三丈拖着******跨过层层的废物桶一边吼一边跑到病人跟前把被子包住了病人上身。转过头用眼神杀了一下赵步理,扭了一下头示意他,意思大概是有多远滚多远。然后和女人说,没事,就看看切口是不是画了,输液还疼么,等会马上麻醉了,不着急。 赵步理本来脸皮很厚,这一下也弄得很不好意思。三步并作两步出去刷手了,他环顾了一下,麻醉师和小云好像此刻都长高了一些,看他的样子都好像在审视的样子,脸越发红了,像个小狗一样的夹着尾巴出去了。 我被控制了,我被控制了,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赵步理在努力用网上看来的方法来催眠自己故作镇定,这也是他一旦出糗就管用的伎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的心里有点奇怪,他在想那个美丽而又优雅的女人,因为她笑了一下,说了句谢谢。赵步理不知道的是,在这样一个冰冷的手术室,她孤立无援的躺在上面,自己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一样,身上绑着各种约束带让她内心极度地恐惧,她有点想哭出来,但觉得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她愿意相信任何下一个和她对视的眼睛,因为她需要一个和她一样的人站在那里告诉她,你很好,我们都在。她笑了,是因为她看到了赵步理的眼睛,脸上唯一露出的部分,在看着她。她觉得内心的恐惧一下子被驱散了,她闭上眼,仔细想那一双眼睛,祈祷在睡醒之后,还能看到他,这个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和她说话的男人。 赵步理安安静静地刷着手,医院对于刷手的要求都不一样,但目的基本是一样的,就是要求在规范的刷手或者洗手之后,理论上手应当是无菌的。每一个医学生在学习外科的时候都学习过,同时也测试过,会每个人在属于自己的培养皿上按个手印,然后进行三天的细菌培养看看能否长出细菌。赵步理这样的蠢货和邋遢鬼自然是在三天后自己的培养皿里发现了一坨一坨的细菌,被同学嘲笑了很久很久。 不过这次他很小心地刷着,一方面也是不想太早回去面对醒着的病人,一方面也还在苦恼自己的愚蠢。他是个很少对犯错误上心的人,不过也可能是之前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他想着大概耗一耗主治医就能来救他了,他就继续当个哑巴,拉着勾然后看着主治医和护士调情,撑到手术结束赶紧回宿舍躺着。 医院是洗三遍手即可,他小心地洗着,然后用水冲掉,小心翼翼地把肘部放低,手抬高,保证肘部冲洗过的水不会反过来污染需要最需要干净的手部。水幕形成之处,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安静的美丽女人。为什么如此年轻却得了癌呢,肚子里有个巨大的肿物,就起源于小肠,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她是因为腹痛,查妇科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临床上考虑她的腹腔生长的是恶性的小肠间质瘤,但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确诊,好在肿瘤位置也比较好手术,所以最后全科的查房建议先手术,确诊了间质瘤之后再评估未来能否用靶向药后续治疗。 二 在麻醉之后,就开始进入了一场战斗。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神奇,两个毫不相识的人见面,坐在一起聊上十分钟,他觉得决定把身体和生命交给你,再给你一笔钱,却让你用刀和手在他体内肆意的挥霍,大部分时候还无怨无悔。往往只有刀口可以让人评头论足,皮肤下面的一切都存乎良心二字。 “哟,消上了,我来的刚好,不早不晚。” 主治医慕容亮踩着小风就进来了,健硕而又挺拔的身段一出现,小云的星星眼就亮了起来,一颗撩汉的心开始骚动起来。 “怎么才来啊,再不来英雄救美你们小大夫就要下手了!” “下手,谁对谁下手,你这么大脾气除了我还有人hold得住?” “神经病,是对病人下手啦!你个有家室的人满嘴跑火车不怕闪了舌头!” 说是这么说,小云的口罩和帽子都遮不住她心花怒放的笑,眼角无数条纹乍现,口罩也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的。 “你们那个小大夫和病人说一会他下手要轻点,亮仔你们就这么教的学生啊,我看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跟你一个德行。”杜姐也趁火打劫狠狠踩了一脚。老护士是小大夫的老师,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还是天敌,另外如果你敢偷拿她们的笔写字你就会死得更惨了。 “恩,有才你不愧是我教……诶你怎么是步理啊,有才呢?这不是他的病人吗?” “呃,他骑摩托车锁骨断了,让我替他。” “啊?这么牛逼的少年。那他以后怎么解决个人问题,你和他住一屋是不是还得帮他……”慕容亮号称外科第一美男,但说起话来也是一点节操和下限也没有,但是干起活来是公认的好手。 “他就断了右边的锁骨,他一般不用右手……” “我是说你还得帮他快进,你想啥呢臭小子,哈哈!” 赵步理有时候已经开始懒得理慕容亮这种没有节操和无厘头的幽默,继续消毒第二遍,小云那边确是咯咯笑个没完,手底下依然麻利地摆着器械,也是一位专业的器护和专业的捧哏集于一身的选手。赵步理眼睛看着自己消毒的区域,擦皮钳夹着纱布有顺序地摆弄着女人的双峰,使全部手术消毒区域不要留下乳房下面的死角。一般老年女人的两座下垂的乳房会比较难拨弄,这个年轻女人的较为挺拔,没有太多问题。 慕容亮已经在穿手术衣了,挺拔的身材包上臃肿的手术衣,依然能隐约感觉肩膀和背部肌肉蕴含的力量。小云痴痴地看着,胡二麻子偶尔不屑地看着小云和慕容亮,然后什么话也不说,盯着麻醉仪器的数值,偶尔调整一些用药。杜姐伺候好慕容亮更衣之后就开始鼓捣各种设备,每个人都忙得很有章法。 赵步理和小云一起把孔巾端正地铺在病人的切口线上,然后就喷手穿衣服了。他可能本能地想弥补自己的冒失。所以一切都又谨慎了一些。他明显感觉小云在帮亮哥的手术衣转带子的时候是笑的,帮他的时候一脸的嫌弃。在医院仿佛都是大大夫调戏中护士,中大夫调戏小护士,而像他这种小大夫,颜值高点比如李有才还有戏,他赵步理这样的就只有做最底层的份了,当然,他也压根不会在意。 主刀陈主任一般会在手术进程开始一会才会来,而前面的开刀,初步的手术都是慕容亮带着住院医师完成,李有才是主治医师们非常喜欢带的住院医,他脑瓜机灵、手活一流、情商超群,而赵步理就有点不好使了,虽然有时候大家也爱训他,但发现他好像就不是手术这块料,怎么骂也教不会,有时候被排他跟着上手术,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在台上大家紧张的时候会一起严肃地奋斗,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这样插科打诨没节操地居多,每天生活在当下的医疗环境下,大家内心多少还是有些不平衡,在台上不打紧的时候也会开开玩笑,而李有才很能活跃气氛,让同事都能很有激情地干活,赵步理就像是一只蠢猫,他不是高冷,就真的只是蠢而已。 目前台上最高级的医生是慕容亮,因此他主持进行患者最后一道核对工作,目的是在开皮前手术室、麻醉师以及医生三方共同确认手术的患者没有错,手术的术式,开刀是左侧还是右侧没有错,防止酿成大错。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也是必须履行的一道职责。 “易米,女性32岁,诊断是小肠恶性间质瘤可能,准备做开腹探查,腹部肿物切除术,手术时间预计3个小时,出血量预计50ml,麻醉师我准备开始了”。慕容亮站在患者右侧那一刹那,仿佛所有的无节操和搞笑都消失了,字正腔圆地宣布手术的开始,让所有人都立刻进入状态。手术灯此刻亮起,两个灯从不同方向打在患者的术野正中间,麻醉师喏了一声之后在一旁维持着患者的生命体征,在高亮度的手术灯映衬下,周围仿佛已经暗了下去,舞台的正中央是一个用生命在舞蹈的女人,她此时的长发随着动作有节律地飘荡,优雅地踩着生命的旋律,死神朝他张牙舞爪地扑来,而骑士拔出长剑立在身前,灯光师调处恰到好处的亮度,舞美适时地洒出烘托气氛的烟幕,而女人的眼神渐渐暗了下去。步理仿佛觉得自己的剑已经挡不住死神了。 “步理,步理!” 说第二个步理的时候,慕容亮狠狠翘了一下步理的胳膊,他才回过神来。自己又开始白日梦了。赶紧拿起纱布和吸引器,准备开皮。 “开皮往往是外科大夫开始手术的第一步,你好好看着。”慕容亮有的时候其实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讨厌赵步理,反而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至善的感觉,觉得他虽然呆一些,但是心眼不坏,有时候甚至会很执念于单纯的善良,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愿意教他一些东西。“刚开始开皮的时候,我总在想,从佛学角度,无论我们自己想的是不是为了她好,我们是不是都在伤害病人。但是我的一个老师也曾经告诉我,古代刽子手执行死刑之前,都会把鸡血抹在脸上,有的说是为了辟邪,也有的人说这是一种仪式,让人在此刻获得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在此刻所做的事情,无关人与人之间的杀害,而只是一种被赋予的特殊权利。我们的手术刀不也是一样的么,你说呢?” 说话间,慕容亮已经划开了一道10公分的刀口,女人的表皮很薄,出血不算太多。女人坚持不想做腹腔镜,与其说在乎伤口的长短,她更想长久地活下去,她还有孩子。而她认为开刀做会更彻底,虽然这在现在看来开刀和腹腔镜做起来可能没有太大差别,但是陈主任还是答应她可以开刀。 三 慕容亮拿纱布蘸了一下,拿起电刀用电切模式垂直切开真皮,赵步理赶紧在对面一手用手掌扒着皮肤,和慕容亮对称地使劲,一只手拿着吸引器吸着电刀烧灼的烟雾和一些皮缘少量的渗血。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味道,这和赵步理小的时候闻到别的小朋友烤蜻蜓的味道最像了。他的吸引器就像电刀的影子一样移动,把血吸掉避免烧成一块块血痂。这个人的皮下脂肪层很少,看上去应该是个经常锻炼的女人,慕容亮快速用电刀划过,避免脂肪过度的烧灼未来出现液化坏死的情况,然后电光火石般在出血点电凝止血,和武侠小说的点穴手法很相似,点过之处只留下一个烧灼的黑点,小血管的出血刹那间平息。 两个人分别提起两端皮肤,慕容亮准确地从人体中线部位划开肌肉,最大程度地保护腹肌,把肌肉层像衣服的拉链一样打开。因为赵步理已经基本掌握了窍门,和慕容亮分别将肌肉拉开,因此中线虽然很难切开,但是在张力绷紧的情况下,电刀的划过就轻易地将纤维切开。最后一层是腹膜,由于两个人已经把腹壁用力上提,因此一般情况下腹壁和里面的肠管已经远远分开,慕容亮轻轻一捅,电刀头就彻底进了腹腔。 “点进腹腔之后,你看到有个小黑窟窿,你就放心了,说明没捅进肠子里,有些腹腔粘连的病人一定要小心地进腹腔。”慕容亮边说边讲,全然没有了刚才那个无节操的风格。 两个人手指头伸进腹腔,提着肚皮,一下子把腹腔全层打开了。大网膜像一只巨大的肥硕的黄色章鱼趴在肠管上面,颗粒饱满的脂肪好像章鱼的吸盘,触手牢牢地抓着胃和结肠,巨大的身体往盆腔坠下去。这是人体的一个天然缓冲垫,另外在有腹部炎症的时候,这只章鱼也能第一时间爬过去,用触手包裹住炎症的部位,然后慢慢消化。如果人们都认为自己肚子里长了一只章鱼守护神,是会感到幸运还是觉得害怕呢。 “洗手,探查!”慕容亮喊道。而这个时候小云已经把事先准备好的水盆端了过来。慕容亮把手洗过润滑之后,对腹腔进行全面的探查和摸索,其实是要除外其他部分还有没有肿瘤,因为,所有人已经都看到了肿瘤。 它就像一朵妖艳的罂粟花,幽幽地绽放在女人的腹中,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它呈分叶状的生长,肉疙瘩从上面参差不齐地蹿出头来,红的褐的黑的混杂着斑驳的色彩,仿佛非常脆弱,一碰就会破碎,又好像吸血鬼刚刚吃饱,嘴角还残留着没有擦干的鲜血。它的根深深扎在小肠的肠壁当中,甚至把三段小肠纠结在了一起。仿佛它是腹部至高无上的女王,三段肠管都是给予她力量的臣民,在她的石榴裙下蜷缩着,正如****的奴隶被带刺的藤蔓紧紧捆住,不甘又无力地蠕动着,身上还因为藤蔓留下一道道白色的血痕,而这些伤痕之中也必定存有女王的种子。三段小肠错综地纠结在一起,托举着罪恶的丑陋的女王。 所有人仿佛都静静地看着腹部中央那一团肿瘤。肿瘤的良恶性只有通过病理才可以确诊,就是说通过显微镜才能给出法律上的判决。但是世界上很多概念都是适用于医学的,就是“美丽的往往都是剧毒的”,就像毒蛇,就像毒蘑菇,就像罂粟花。像这种颜色斑驳,红似血色玛瑙的分叶状肿瘤,对于临近器官有侵犯的肿瘤,大多都是恶性的。 “可怜的孩子,才这么年轻,你们几个好好弄别着急,国安的球那么臭我正好躲一躲。”杜姐抬了一下眼皮,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我正好也不用去看孩子,孩子都习惯了,我一会去给孩子打个电话,你们别急。小亮你慢慢分着,我不催你叫主任。” “叫主任,手术不好做,咱们小心一点,步理,小心点别碰破瘤子。”步理可以看到慕容亮的眼神,好像有一丝兴奋,但是又好像有一些悲悯,很难以形容。而且这是头一次步理看到慕容亮这么早叫主任。一般情况下主任是手术的全权负责人。但是主治医师也是有能力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操作,也是十分合理的。慕容亮一般都会先分离上一阵子,然后关键的部分有主任在场之后配合主任完成。但是这次,他首先选择了最保险最稳妥的方法。只有一个原因,这个瘤子看上去太脆弱了。 一般这样看上去很容易出血的瘤子,一旦出血都十分难以收场,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肿瘤破损会让大量的肿瘤细胞播散到腹腔的各个角落,即使再认真冲洗,未来也依然有新的肿瘤细胞终止在腹壁上,生根发芽,发生复发或者转移。从肿瘤的治疗角度,如果一旦瘤子破了,即使病人恢复再顺利,手术也是十分失败的。 慕容亮抓起一段肠管,示意赵步理像他一样拉好,然后他拉起另外一块肠管,两个肠管之间有一些粘连,离肿瘤比较远,需要先进行分离。在两个人不同方向的牵拉下,肠管之间立刻出现一层薄如蝉翼的膜,这是正常的结构。 “有的时候手术就像是吃饭一样,你吃披萨饼的时候怎么拿,你一只手有时候很难拿起一角披萨,但是如果有人能帮你压着旁边的,你有个反向的牵拉,就很容易把粘在一起的病拿起来。”慕容亮有时候也会这样文艺一下,赵步理心里想说,如果他说手术像吃饭,可能护士只会觉得他恶心。所以俗话说得好,长得好看的人说什么都对。 没错,他的眼睛顺着慕容亮的电刀滑下去,看到组织之间那些丝丝拉拉的牵连结构,就是组织之间相互连接的纤维索条。两个器官之间不只是相互挨着的,往往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科大夫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联系斩断,把需要切除的部分“解剖”出来。而这些丝丝拉拉的结构,就像披萨饼几块之间相连的面糊和芝士一样,软绵绵的,只有把它们绷得紧一些,才容易用刀划断,而如果松松垮垮的,就会粘在刀上,随着刀越拉越长。 四 电刀轻轻地在组织之间点击着,慕容亮刀法很准,每一次都能点击在纤维最紧的结点上,点开之后随着钝性的电刀头轻轻的推搡,会把疏松的组织自然推开,而进一步剩下的又是最紧的一条纤维,再烫一下让它断裂。如同撕卷心菜的时候我们把外面疏松的枝叶首先撕下去,最后剩个硬菜梗我们用刀切一下。电刀优雅平稳地走在疏松的膜上,因为层次非常正确,所以没有碰到任何大的血管,气化的作用让这层薄膜呈现出疏松的气泡感,像乳白色的蜘蛛网一样。在合适的张力下,电刀宛如一位妙龄的少女,她对着蛛网呢喃地低语,白色的网未触先断,从她的两侧柔顺地分开。就这样一层一层的,两个肠管之间正常的间隙就被打开了。 “这是外科医生都常常说的层次,当然我也做的还不是那么好,但是你看,层次走对了,就不会伤到血管,而无论深了浅了都会伤及到周围的器官,走对层次就好像走独木桥,好的外科大夫可以从一边走,而像我就需要两边一起走,向中间靠拢,这样不容易一边走深一边走浅,你慢慢体会这种感觉。主要靠钝性的推拉,少部分靠锐性的切割,组织自己会给你提示。” 小云有序地递给慕容亮钳子,剪刀之类,什么东西快用完了杜姐也基本会在第一时间直接打到台上。每把钳子打到手心的时候都是清脆的“啪”的一声,伴随着手术室麻醉仪器显示的心跳声,不时传来口令和电刀悦耳的滴滴声,尤如一台用来雕刻生命的交响乐,美丽女人在舞台的正中间有节律地灵动地跳跃着,如吞食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内心渴望着救赎。 赵步理的手拽着对侧的肠管,在慕容亮的指点下试着拿着长镊子夹着慕容亮烫的地方旁边,给他一点所谓的张力,同样是让局部更紧绷电刀容易切开。他仿佛感觉每一次的切割都不是来源于电刀,而来源于手下组织轻轻撕裂的感觉,那一刻的感觉妙不可言,他仿佛内心爆发出一种爽快感,不知道手握电刀的感觉未来会是如何。 “做得怎么样了?” 陈主任浑厚的声音传来,这样有辨识度的声音大家虽然一下就知道了,但是为了表示对这位大能的尊重,还是齐刷刷地转过头去。 慕容亮的气场自行地降下来,声音也放低了一些。“陈主任,其他地方都分得差不多了,但是瘤子太脆了,没敢碰,您来吧。”说着就自行想绕到赵步理的助手位置。 “没事,你在那边吧。”陈主任非常淡然地说。 “好的,谢谢主任。”慕容亮轻轻地,却是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谁都知道这时候是主任要带着年轻医生做手术,作为年轻医生的助手手把手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赵步理往上挪了挪,给主任让出来他的位置。他因为挪到了病人的头侧,正好看到了帘子后面的美丽女人,两只眼睛贴着胶布防止长期不自主睁眼带来的干眼症,安静地睡着。他的视线又回到病人的腹腔,他很难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一个那么美,一个那么丑陋。 为什么手术是对人的伤害,但确是世上人类公认的至善,往往就是由这些至恶的疾病所决定的。之所以我们愿意去背负着伤害人,甚至可能杀死人的风险也要去手术,正是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要清楚这些极度丑陋,丑陋到危及生命的存在。赵步理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因为他干外科也很多年了,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去理解手术。 “步理,你觉得这个病人应该怎么切?” 赵步理一下子被问懵逼了。什么叫怎么切,我哪知道怎么切,你们切我看着就是了。便随口附和了一下“我觉得应该都切了,连着下面三段肠管。” “和我想的一样。”陈主任并没有表现出十分开心,但是略微点了下头。 “你说得很对,其实临床上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是与对,我也可以把瘤子完整地分下来,但是即使瘤子不破,你看肠壁上那些白色的东西,都不好说是不是侵犯了。病人第一次手术的机会是最难得的,才这么年轻,不要给她留下任何隐患。” 其实赵步理内心根本就没有这么想,他只是内心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女人是美丽的,任何与瘤子相连的都是丑陋的,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拿走,那样他才会觉得内心是安心的。他并没有从其他角度全面地想问题,他只愿单纯地希望她一如既往地美好。 主任捋了一下肠管,决定好合适的位置然后开始处理肠管的血管,合理的顺序是处理完小肠的系膜血管之后,把肠管切断,然后再把肠管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接在一起。陈主任提肠管的动作虽然看上去和赵步理没有任何不同,但是稍微变化的角度和力度,都让小肠舒展地展开成一个平面。慕容亮的电刀开始飞速地在系膜上游动。 碰到血管的时候,主任和慕容亮两个人会非常熟练的用直角钳掏过,然后用丝线结扎血管的两端,再从中间断开,最后剪线。小云的手好像哪吒一样可以同时拿出不同的器械精准地分别放在两个人的手里,感觉效率比刚才快了一倍还要多。两个人没有一个费动作,就是机械地像蚂蚁一样一点点消化系膜的血管,直到最后系膜啃出来一个大洞,视野当中只剩下肿瘤和她缠绕的三段小肠。 赵步理基本看不懂手术,他也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只是拿着吸引器默不作声的吸烟,这个时候的他居然没有那么想回家,他看着手术台上的操作,他心里有些兴奋的感觉。当每一次主任用丝线打结的时候,他看着那种食指压着现结向下滑动的感觉,内心就一点点被撩拨着。 “这个你打吧。”主任掏过线,递给步理。 步理心中一惊,想了想自己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机会,不是断了就是不紧,反正总是需要别人重新再帮他加固的。这次,他仿佛不知道哪里来了自信。有些颤抖地接过线,像主任一样用手指掏过线头,熟练地绕过手掌,抓住线的两端,试着用手指往下慢慢地压下去。试着像别人教他的抚摸女人秀发的方法,以食指的指尖作为受力点,让两根线收紧。 “啪” 线断了,结扎的血管哗地一下开始飙血,像小喷泉一样冒着鲜红色的血液,甚至喷洒到皮肤外面来。胡二麻子和护士们转过头去,陈主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慕容亮赶紧用吸引器吸着局部的血,试图找到出血点。陈主任的衣服上留下了一道血线,由无数多的红色小圆点构成,不是一条完整的线条。 “你到底怎么练的打结啊!你手压那么使劲干什么啊!”慕容亮开始吼起来。 赵步理懵在一边,也不知道说啥,就只是待着。他长了教训,有些蠢货在尴尬的时候,往往不说话还能好一些。他心里越发地难受,倒不是因为自己笨,是因为他真得想对一个人好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像一只瘸了腿的小狗,站在自己的主人面前,他只能叫,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 很快慕容亮就找到出血点,并且上了钳子。重新结扎,不过这次大家没有考虑让步理再试一次。在医学上,会通过机会不断进步,不过这次机会没有了,今天也就没有了。台上只有检验的机会,不是训练的地方。 这是很常见的出血,不属于需要大家惊慌的事情,和拳击运动员被打了一拳一样,你只需要转过头继续打过去就好,手术和打仗一样。为什么平时和和气气的慕容亮会突然发飙,也许是因为内心的紧张和恐惧,也许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啊。当你在看到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类受了重伤躺在地上,你不知道怎样救他,你会着急,你会害怕。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帮你,但是却帮上了倒忙,你就想对他吼,让他滚远点。你希望谁能来帮忙你,帮帮那个遇到危险的人。 人的一项本能,就是呐喊。 不过对于主任来说,仿佛一切都云淡风轻不曾发生。他的一生见过了许多生死,每天都走在钢丝线上,过独木桥的时候自然不会觉得害怕。 肿瘤再次露出了越发狰狞的嘴脸,原先的肉红色转变为了幽暗的紫红色,妖艳的花朵变成了邪恶的巫婆,好像伸出带有长长指甲的手试图去抓住女人的身体。不过可惜的是,她所能抓住的就是她所侵占的三段肠管,可能会永远地从这个女人的体内消失,封印在福尔马林中长久地待下去,终究有一天会灰飞烟灭。 再过了半个小时,在主任和慕容亮的娴熟配合下,手术结束了。主任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留下慕容亮带着赵步理关腹。慕容亮仿佛刚才也没有骂过赵步理,继续安静地一边做一边讲着。 “这个拉锁我们得给她装的好看一些,她未来能看的就是这个口子了”慕容亮又开始恢复了原先的轻松和幽默,一边做着一边讲着。“小云你看你那么瘦,如果做手术肯定更好做。” “别逗了亮哥,我A4纸横过来差不多了,人家最近都胖了”然后继续咯咯地乐着。麻醉师开始准备让病人苏醒,杜姐反复地核对着每一个器械和每一块纱布确保准确无误。 随着最后一声“咔嚓”,皮肤钉合完毕了,看上去口子也并不大。赵步理看看时间已经接近12点了,而大家好像并不像开始那样焦虑。好像每个人又不会受到这个女人的影响安心地做该做的事情,同时又带着一丝怜惜在给自己的付出安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到底他们是冷血动物,还是热血的人呢,感觉两种属性又同时存在着。 “滴滴滴滴——!”报警声顿时响起。 “心跳没了!”胡二麻子首先反应过来。 (不负责任连载中....) 北京哪有看白癜风的专业的白癜风治疗医院 |